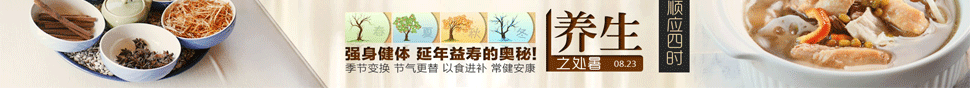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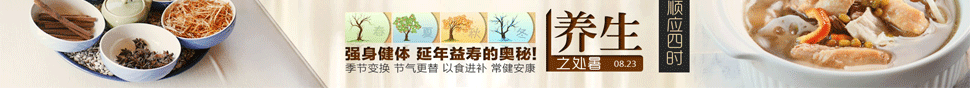
横屏观赏周力作品《春》之一
《春》之一,布面综合材料,xcm,
花园印象周力拿着园丁剪刀、穿着一身牛仔工装在花园里走动,她的目光时而穿过低矮的玫瑰灌木丛,时而伸向树冠深处。南方的苔藓悄悄吐纳晨雾,四周的枝梢因为鸟群的停驻飞离而发出轻颤,河水正倒影着一棵历经多年而垂向它的*花梨。花园正在一种难以被把握的变幻中,一层一层的醒来。这样的日常便是周力在广东美术馆新个展“格林迷踪”的创作之源,她画面中氤氲的光色与看似写意的线条,并非来自艺术家脑中的想象或随机的行为,而是对与实景时空亲密接触的瞬间捕捉。仅从这种观察方式而言,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年印象派所映射的某个交汇点,如评论家艾伯特·沃尔夫对早期印象派所做的表述:“艺术家画的不再是一个海景或一个人物,而是画一日中某个时刻的印象。”到后来,晚年的莫奈对花园和睡莲的描绘,形象又进一步的完全融于色彩中,由此影响了之后的抽象艺术。《桃花源》粉色-线之五(局部图)笔墨力量从一种经典但也较为粗略的分类去看周力的作品,毫无疑问会被归类成抽象绘画,但她画面中那不可忽视的笔墨线条又引入了另一条超越该分类法的脉络。在中国古典艺术的人文传统中,并不会去谈抽象和具象之分,高居翰在进入中国山水画时使用的是“大自然的变形”的概念,由这个变形最终进入笔墨背后的气息和法,这是东方特有的经验主义的感知方式,超越理性与感性、具象与抽象的对立二分法。摄影:WenjunLiang
造型:SharonChiu针织上衣及长裤,Herme?s;长款印花图案大衣及背心长裙,UMAWANG;高领上衣衣、背心裙及长款大衣,PRADA
类似的,周力的画面里似乎有一种气息,可以容纳诸多不同的元素——轻薄透气又交融多变的色彩、硬软相接的线条、环形、圆点。周力非常喜欢水,当人们试图用女性主义去解读她的作品时,她则更乐意将其中的阴性能量与水的智慧所相比拟。但从目前的相对层面来说,中西美学背后的文化驱动力和思维方式还是非常不同的,周力在感受现今外部世界的现状时,看到了调和这两者的困难,这同时或许也暗示着她一直不愿意主动进入任何一种既定的艺术风格或流派分类中。荒原创造若将周力的绘画和类似波洛克或康定斯基这样的抽象进行比较, 价值似乎就是发现它们的难以比拟性,我们会发现其背后的身体性和文化触发点的迥然不同,或哪怕是同样留法的那支由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等人所引发的脉络,也都只是从史的归纳角度去接近一种参照系,哪怕是将她同诸如施拉泽·赫什阿里这样的也来自东方的女性抽象绘画艺术家放置在一起,虽也有氤氲色彩、或波斯或中国的传统书画笔墨背景、也同时做装置艺术,但我们其实都只能借由这些表面的检索标签来发现她们,但一旦仔细进入,她们各自都是一个个 的完整宇宙。横屏观赏周力作品《春》之八《春》之八,布面综合材料,xcm,
皮力认为“周力的绘画把我们导向了一个长期被精英和理性的抽象绘画遮蔽的、感性与经验的荒原”。荒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失去参照系,意味着“迷踪”,意味着能得以完全忘我的、具身的进入到此在。荒原就是创造,就像四季与母亲、就像涓涓细流淌过埋藏着种子的泥土。只于一花一叶中,开垦出生命的花园。对话周力Q:你最近在广东美术馆的新个展“格林迷踪”中,有一幅名为《.02.17》的作品可谓是万绿丛一团墨。你作品中的“墨”的元素,在之前更多是以黑色线条出现在画面中,而这次却采用了大面积的黑色笔墨来呈现,你平日也研习书法,不知是否与你对中式的墨的理解有关?此外,这幅作品以日期命名,想必也同去年疫情下的情绪节点有着直接关系?“格林”本身虽是英语“绿色”的英译,但也似乎在双关指涉“格林童话”,而这部童话本身就包含了暗黑的气息。所以在进入绿色之前,很想请你先聊聊这“墨与黑色”的话题。A: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我 收到的一个关于“墨”的问题。“格林迷踪”这个展览题目是策展人鲁明*提出来的,它很巧妙的解决了展览空间原先的局限,因为广东美术馆是一个老馆,层高比较低,不是那种开阔的白盒子,而我的作品的尺寸又很巨幅,所以最一开始对于这个空间我是有所顾虑的,但有了这个题目之后,原先空间上的劣势由此转变成了优势,因为是“迷踪”,所以反而越狭窄越好。同时,这个题目把年的魔幻感和困境表达的特别清晰:《格林童话》本身是一个挺暗黑的文本,不仅仅是那种给儿童看的甜美童话,里头的寓意其实真的只有成人才能看懂。你问到黑色和墨,这里面有个东西方美学的差异,在西方,纯黑色是没有反光的,它吸收消解了所有色彩,纯黑代表一个 ,而中国绘画则讲“墨分五色”,其实墨根本不止五色,它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我认为墨不是为了要消失,它的存在反而是为了凸显,它以一种内省的方式让人们去观看。《.02.17》是去年封城的时期创作的,那时候被一种惶恐、一种忽然到来的不知所措所笼罩。到了《.05.17》那幅的时候,情况逐渐在缓解,人们已经开始有所走动,生命的绿色从黑色之中萌生出来,而且5月17日是我大儿子的生日。但如果要说到绿色和自然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春》系列,其实早在年就已经开始创作了,和当年的《桃花源》系列是同期的。Q:绿色或自然的灵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的私人花园?A: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花园,而是人和自然的这种亲近的过程。去年由于疫情不能出门,阿姨又不在,需要我自己去打理这个花园,你照顾的越多、付出的越多,它慢慢给你的回应也越多。每天早上六点我就起床了,趁着阳光没出来,我会跑去花园看着它慢慢醒来,一直到八点钟太阳完全升起来,在这两个小时里,花园的光和颜色可谓是千变万化,美到我一直想要去捕捉这些时刻。包括你前面也看到的小鸟,我每天早上就坐在那个草坡上看鸟、听鸟,它们也不怕我,就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的,与花园的相处中有太多这样具体的细节了。Q:你的这番描述让我想到你曾经对于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的看法,你说你的画面中其实有特别多具象的成分,我想这里的具象也许指向你与描绘对象之间那非常具身的、真实的交流经验?A:这个解读的角度很有意思,可能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画面中的硬边线、软边线的问题,光线瞬间一变,硬边线就这么出现在眼前,那是非常真实的。就像印象派绘画里的光色根本不是画家凭空想象出来的,你要是真的在那里,阳光一出来,你就知道它们其实完全是写实的。包括中国古代绘画,你以为那些树的形态可能是捏造的,但去江苏那些山林看一下,你就知道它们也是很写实的。Q:你在年的展览“心原”中呈现过另外两种也很具有代表性的色调——蓝与粉,它们在展览中呈相互对照的关系,这两种颜色反应了当时你的何种心境与创作阶段?A:我的绘画总体有三大板块,城市空间、人文空间和自然空间。创作“心原”时我站在人文的位置上,我回到了“中间”,而在这之前,我是完全站在窗前朝着外面望的,但“心原”是同时向外看和向内看。虽然我之前不愿意多说,但色彩毫无疑问是有一定取向性的,比如这里的蓝色带来的就是一种宁静,粉色可能更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它很柔和、很温暖。当然,蓝色的宁静中也有爱,但它是更雄性的那种爱,也代表着一种希望。色彩具有一种暗喻,但它又不是全部。Q:你的作品里经常同时包含很多不同的视觉元素,比如线条和色彩、甚至是不同质感的线条,但你都能比较自然的将它们融合在一块画布上,你是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A:其实线条和色彩是很难在一块的,它们如何才能融合在一块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很多人会问“你是怎么把软的线条和硬的线条放在一起的呢”,对我来说,这有点像把理性和感性结合在一起的感觉。Q:你的作品尺幅都很大,你如何看待大画和小画的区别?A:其实好画是不分大小的,比如我上次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看弗朗西斯·埃利斯的展览,他的小画都很精彩。但大画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的,它更需要宏观的眼光和控制力,才能去把握住那个整体。Q:你有段时间一直会创作和环状有关的作品,比如《生生如环》,环状这个形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A:环状的形态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线条的“显与隐”,在画面里你好像看到它要断了,但它又回来了,这和我们的生活很像,包括生育,或是大自然和四季,春天逝去了,但第二年它还会到来,生命就是这样的循环、生生不息。Q:你提到孩子很多次,我记得你创作过一个声音装置,是你孩子的胎音?你认为自己成为母亲的过程,对你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什么特别的影响?A:这个过程让我变得更有责任感,爱的意义由此变得更为具体化。胎音的作品当时在余德耀美术馆展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个过道的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子宫。Q:你作品中那种若有若无的永续生命力,让我想到老子所说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隐性力量,你如何理解女性创造力的价值?A:我认为艺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这种永续的生命力。很多人也经常提女性主义这样的说法,但我想等到哪天我们不提这个了,两性才算真的平等。水既能包容滋养万物,但它凶猛时又能摧毁一切,而且失去了水,谁都无法生存。我下一个系列可能就会和水有关。Q:你是首位与白立方合作的中国女性艺术家,你如何看待东方女性艺术家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地位现状?A:说实话,目前来看中国女艺术家在这个参照系里是没有地位的,大部分情况是,他们(西方)会把你当做少数民族,或者说出于文化上的好奇心或意识形态的主张而摆出某种姿态来
